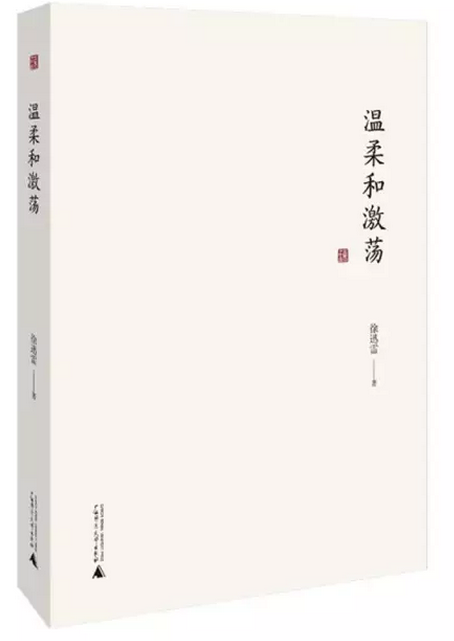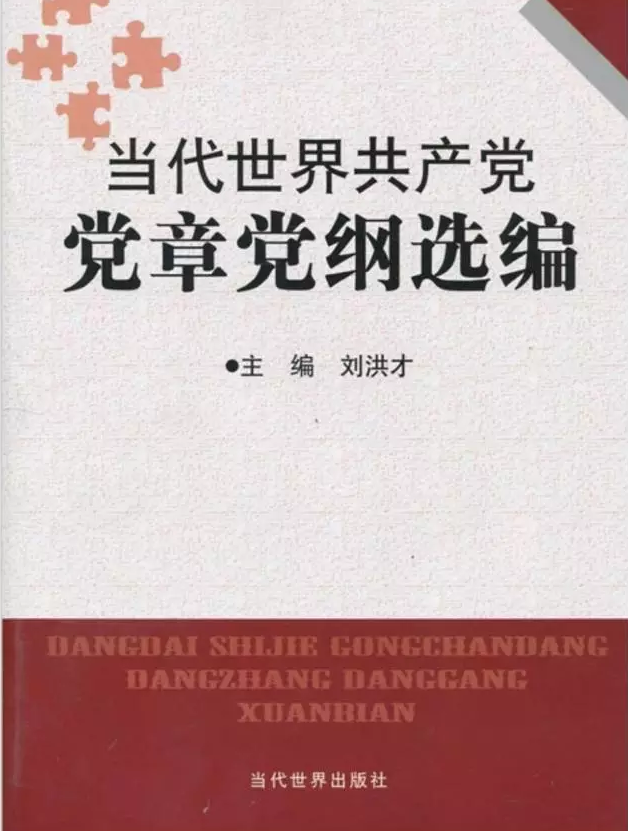
普拉昌达住豪宅被批“背弃社会主义”——这是2012年2月1日《参考消息》一个报道的标题。报道援引的是法新社的消息:
曾在尼泊尔领导叛乱的毛派领导人普什帕·卡迈勒·达哈尔,今天遭痛批为背弃毛派路线,因为他搬进首都加德满都的一栋奢华豪宅。
化名普拉昌达的达哈尔是前共党游击队员,后来发起对抗尼泊尔王室及政治精英的“人民战争”。
这栋邻近市中心的顶级出租豪宅占地1500平方米,拥有15个房间,还有可停放超过12辆车的停车场。
前毛派领导人、政治分析家卡纳尔表示:“毛派成员背离该遵守的目标,他们过去奉行社会主义,现在却臣服于资产阶级势力。”“普拉昌达现在拥有权力,只想着积累财富并过奢侈的生活,他选择的这所住宅就是证明。”
普拉昌达领导的尼泊尔共产党(毛派),曾经是货真价实的“毛派”——“毛主义”,而不是“冒牌”。“普拉昌达”这个名字,尼泊尔语的意思是“愤怒之火”。如今年届六旬的普拉昌达,出生在尼泊尔南部的农家,大学毕业后曾在公立学校任教。1996年,他在“目睹乡村穷人过着悲苦不堪的生活”之后,决心发动武装革命;他“带着满腔怒火”,和支持者一起从首都加德满都转入尼泊尔西部的深山密林,走上“武装斗争”的道路,最终于2008年推翻了沙阿王朝。普拉昌达曾经短暂出任尼泊尔总理,现是毛派尼共主席及代表加德满都选区的国会议员。
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变化发展的历史曲折复杂。尼泊尔共产党成立于1949年4月,地点在印度的加尔各答,其宗旨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,争取在尼泊尔实现社会主义。半个多世纪来,尼共先后分裂成多个互不隶属的政党。后来逐渐出现两个最大的派别:一是在合法斗争中发展壮大的尼泊尔共产党(联合马列),二是主张武装斗争的尼泊尔共产党(毛主义),即“毛派”——“毛派”坚持极左路线,坚持暴力革命,甚至被国际社会列为“恐怖主义组织”。
我手头有本厚大的《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选编》(刘洪才主编,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,定价200元),这是为读者系统了解冷战后各国共产党现状、最新纲领及理论政策主张而翻译编纂的,重点选取了国外较有影响的47个共产党的党章党纲。收入其中的尼泊尔共产党党纲,是尼泊尔共产党(联合马列),而不是尼泊尔共产党(毛主义)。
尼泊尔共产党(联合马列)简称尼共(联),于1991年1月由尼共(马)和尼共(马列)合并而成,所以称为“联合马列”。该党认为,美国的霸权主义是导致世界动荡不安的根源,他们要反对和改变“半封建半殖民地”的形态。在冷战结束后,尼共(联)根据尼泊尔国情,与时俱进调整自身的政策纲领和斗争策略,参与执政,与其他政党一起,维护和巩固尼泊尔的多党议会制,它成了尼泊尔制宪会议第三大党。2011年2月3日,尼泊尔共产党(联合马列)主席卡纳尔(又译卡奈尔)当选新一任尼泊尔总理。原来不仅仅是“枪杆子里出政权”,不用大规模流血牺牲,而是通过票选,也是能够上台执政的呀——这就是真正的“选票比子弹有力量”。
但普拉昌达不一样,他喜欢斗争,喜欢革命,喜欢流血。他拉起队伍走入山头、开展武装斗争的时间是1996年,这时距离1927年中国的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已经过去了近70年,距离1989年苏联解体、东欧剧变、冷战结束也已7年。当时在首都加德满都的普拉昌达,坚持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应当向“资本主义”主流政治妥协;1996年2月13日那天,他和他的军师以及一些支持者从加德满都出发,从城市走向农村,开始了武装斗争。
“1952年,我出生在尼泊尔博克拉市附近的一个小山村。‘普拉昌达’只是我的外号。当年在游击队里,为了掩护自己和保护家人的安全,我们每位领导人和指挥官都有一个外号。虽然我的家族属于最高种姓婆罗门,但我和马克思、列宁一样,背叛了自己的种姓和阶级。”普拉昌达曾这样自述道,“我们发动革命,就是为了推翻‘封建制度’,打破压迫尼泊尔劳苦大众的种姓制度,解放低种姓人民。正因如此,大批低种姓少数民族群众加入了我们党。在内战期间,我们的大部分高级将领是少数民族同胞。”
革命时期的普拉昌达,几乎就是白手起家,各方面条件确实很艰苦。他回忆说:“当时,我们的队伍只有一百来号人,唯一的武器就是两支破旧不堪的短枪,其中一支还不能用。我们联合当地的贫苦农民,用自制土枪袭击防卫薄弱的偏远警察哨所,缴获他们的武器;也想方设法从黑市上买一些武器;后来索性培养自己的工程师,办地下工厂,自造武器。罗尔帕县是‘人民战争’的起点,因此,同志们亲切地称它为‘尼泊尔革命的延安’。”
普拉昌达并非草寇,他读过大学,从农业学院毕业;他样子像学者,自己也并不拿枪射击。从中学时代起,普拉昌达就接触了共产主义理念,对中国革命尤其感兴趣。他打游击、建立革命根据地,还真是学了毛泽东领导革命的那一套,而且很有成效:“在罗尔帕,我们建立了革命根据地,外人要想进入,就必须拿到我们开的‘路条’。在根据地,我们建立起自己的人民政府,设立了人民法庭、税务机构,行使政府权力。此外,我们还开办了许多中小学校,战士们和贫困村民的孩子都可以免费接受教育。为帮助村民解决经济困难,我们建立了金融合作社,办起了各种小型工厂。这不仅使游击队在衣食住行方面实现了自给自足,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,满足了村民们的生活需要……”“毛派”游击队走的正是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道路。
不到一年,普拉昌达就发动了上千次袭击,由于这些游击战看去就是小打小闹,所以尼泊尔政府起先是不屑一顾,认为他们不过一小撮“恐怖分子”而已,但几年过去,到了2000年,政府军恍然发现,普拉昌达的游击队已人数过万,这个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内陆国家的半壁江山几乎都归了他。这大概就是“天翻地覆慨而慷”。
美国在2001年宣布普拉昌达的反政府武装为恐怖组织。在西方媒体的笔下,普拉昌达在尼泊尔所干的是“10年叛乱”。作为“反政府武装”,普拉昌达的暴力革命最终造成了1万6000人丧命的结果。武装斗争结束后,普拉昌达终于成功“进城”;很快地,在尼泊尔大中城市几乎所有的公共建筑上,都挂上了普拉昌达的肖像、写上了尼共(毛主义)的宣传口号。普拉昌达同样喜欢组织大型集会,在加德满都几次民众集会,每次都有数十万人参加。
自发动武装斗争之日起,普拉昌达和他的战友们就“失去”了私人财产,过着共产主义般的生活。尼共(毛主义)的领导人曾发誓不保留任何私有财产,他们把私有财产交给了党。那时领袖们没有工资,而是每月报销一次日常办公和生活开支。作为游击队的“一把手”,普拉昌达和士兵休戚与共,一起忍受着极其清苦的生活,伙食是农民常吃的豆子糙米饭;一年到头只有两三件衣服,此外几乎一无所有。
普拉昌达2008年6月“进城”后,起初在加德满都的生活依然“寒酸”,饭里有咖哩鸡肉算是“奢侈”。从“进城”,到当上总理,到2009年5月4日宣布辞去总理职务,其间普拉昌达得到了总理的工资,他曾向BBC尼泊尔分社记者宣称,自己工资将属于国家和人民,“除了留下一些作为维持日常的开支,工资将被存放在党的金库里”。连自己的工资都属于国家和人民!普拉昌豪情满怀地说:“我们充分相信人民。我们忠于国家和人民。任何人都不能把我们和人民分开。”
但环境改变人,蜕变虽不是一瞬间、一夜间,但在新的环境中,悄悄地总在变化。进城后,尼共(毛主义)领导人自然而然地开始穿上了西装和皮鞋。“这是体现我们党形象的需要,是‘革命的需要’。以前,由于经费缺乏,我们的制服都是自己生产的。我们也穿从中国进口的T恤衫,中国货既便宜又耐穿。”普拉昌达曾这样对中国记者说。
政治人物,大抵随着权力的变化而变化。往往是权力让变化来得很快,因为权力带来各种各样的需要。比如安全的需要:革命时期,可以睡在农民家里、睡在草窝里避免被发现、遭暗杀,革命成功后,当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,能这样躲避、防止暗杀吗?显然不行。普拉昌达曾被称为尼泊尔最神秘的共产党人,在“打江山”之际,绝大多数尼泊尔人只听过他的名字,未见其真容。在10年内战中,普拉昌达曾在印度秘密居住了5年多时间,以确保自身安全,这倒很像本·拉登藏在巴基斯坦;而印度是把他们这个反政府武装列入恐怖组织名单的,是侨居印度的尼泊尔人秘密保护他。“打江山”结束了,如今在首都“坐江山”的普拉昌达,则需要豪宅及大批安保人员来保护。
独领风骚三五年,威权中人谁不变?崇拜武力,夺取政权;夺取政权,崇拜权力;拥有权力,崇拜利益……这是路径依赖,亦是人性基因。现在回首看去,普拉昌达当年上山打游击,其真正动因还真不见得是“目睹穷人生活悲苦不堪”,恐怕主要是不满当政者长久掌控权力而没有权力分享。他的“愤怒之火”更多的是因自己、为个人而生,由此发动的“十年革命”,结果让那么多人死于非命。为人民服务、为人民谋幸福最容易成为旗帜,同样也最容易成为幌子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以成为响亮的口号,实实在在为自己谋利益则是权力的实质。
有媒体曾这样报道:原尼泊尔反政府军一名23岁的士兵,正在南部乡下的一片农田里忙着埋水管,他说,“放下枪的感觉很好”。而在他们拿起枪杆子的日子里,情况完全不一样。2001年1月26日,加德满都以西100公里处的本迪布尔警察局遭到炸弹袭击,3名警察受伤。这是哪些拿枪杆子的人干的呢?当时的尼泊尔王国政府对普拉昌达和他的十几名党员提起诉讼,指控他们参与袭击,犯有叛国罪。8年后的2009年6月,尼泊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作出判决,宣告普拉昌达无罪,因为2001年以来的历届政府都不能提供足够证据来支持这一指控……在今天,你说普拉昌达愿意自己像警察局里的警察那样挨炸吗?被明杀或暗杀的可能都是完全存在的,所以,躲进深宅大院最好最安全。
然则,当过尼共(毛派)领导人的卡纳尔,依然毫不客气地批评普拉昌达们:“在当今情势下,变成如同议会政治中的一员并不令人意外。这些人只将改革挂嘴上,不会付诸实行。”从草房到豪宅,是必然趋势。人们不免要想:一所领导豪宅,几多百姓血汗?权力的快感,通常都要建立在百姓的痛苦指数之上;而权力的安稳,更要建立在百姓的血汗代价之上。不久前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有个报道说,盖洛普健康调查表明,许多中国人情绪都不够高,富起来但幸福感不足:对于自己的状态,感觉“蒸蒸日上”很幸福的只有12%;“比较挣扎”幸福感很一般的占71%,这比例与海地、阿塞拜疆和尼泊尔差不多;感到“痛苦艰难”不幸福的占17%,比例高过苏丹、巴勒斯坦地区和伊拉克……这是有关“健康情绪”的询问式抽样调查,其实就是把“幸福感”分为好、中、差三类,不一定很准确,只是一个参考维度;那么,在3000万人口的尼泊尔,感觉自己幸福感很一般的人是不是真有七成,真实情况不得而知,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:有些领导人的幸福指数确实在“蒸蒸日上”。
(原载《2012中国杂文年选》,收入《温柔和激荡》一书)